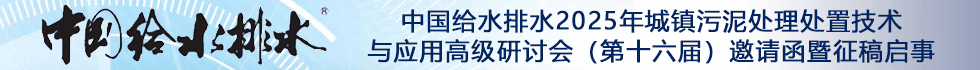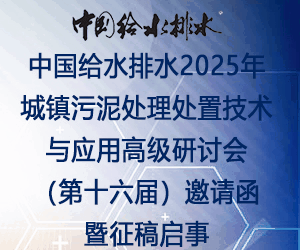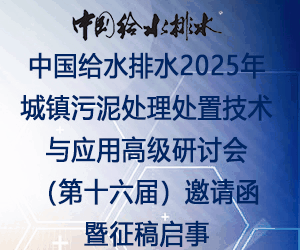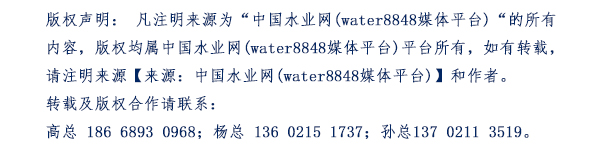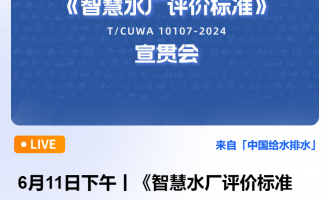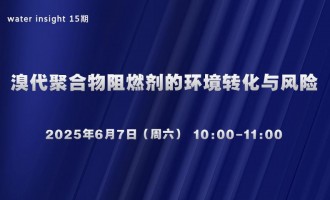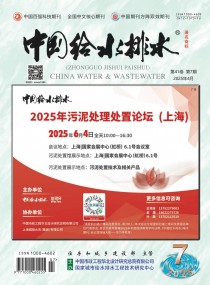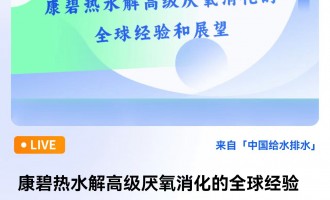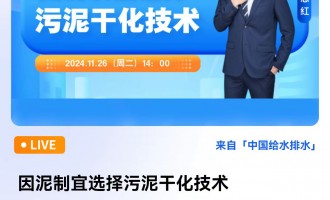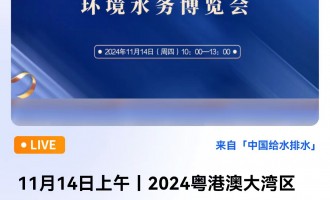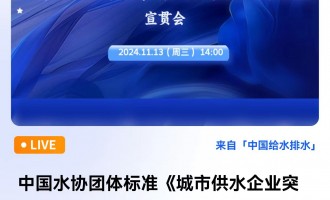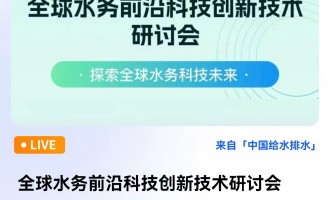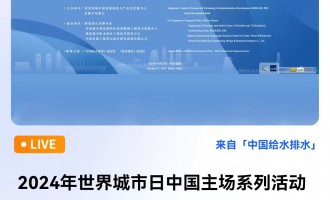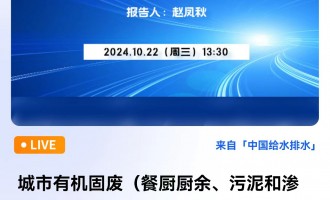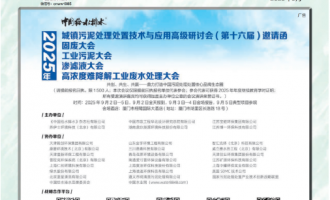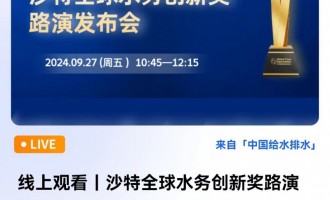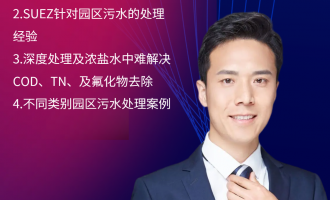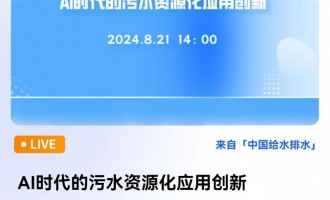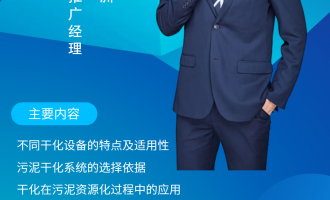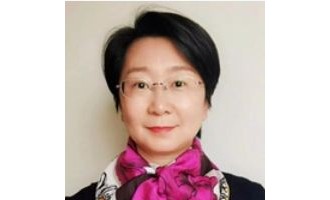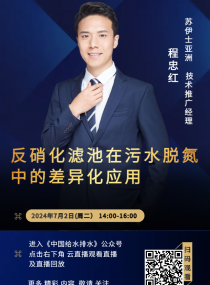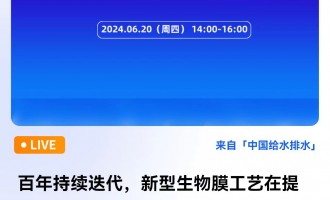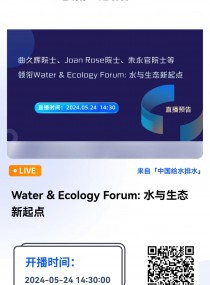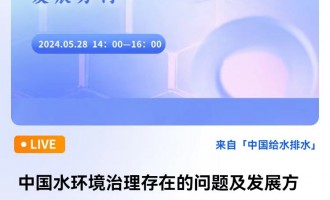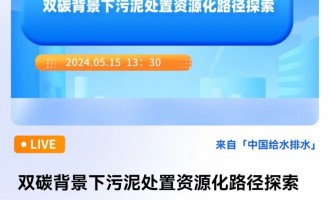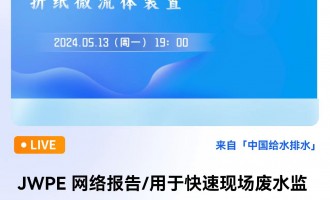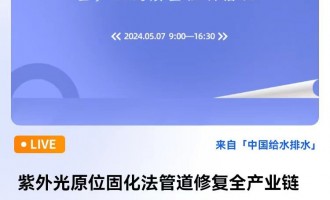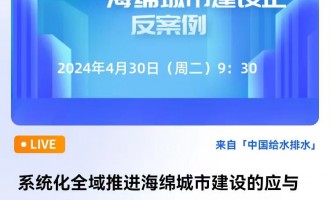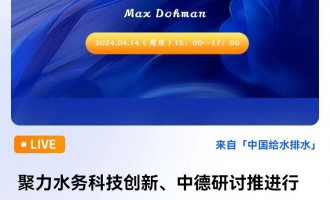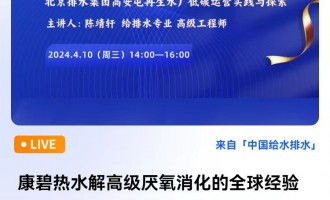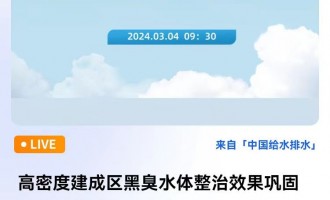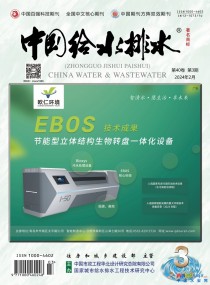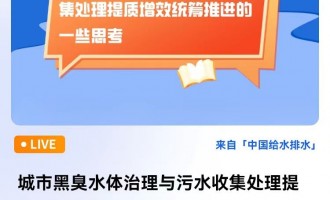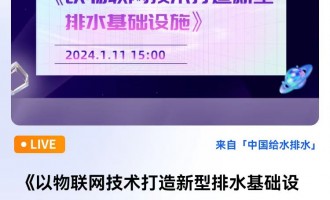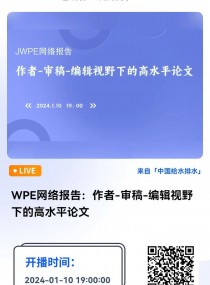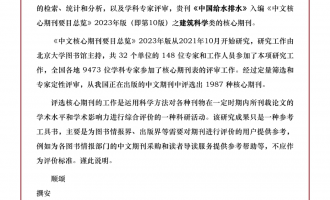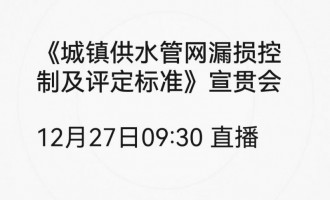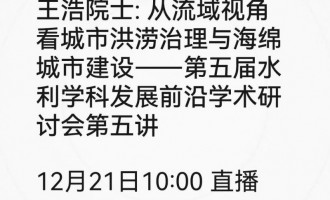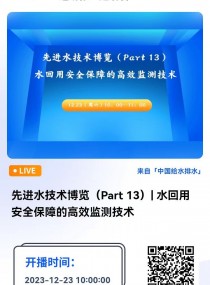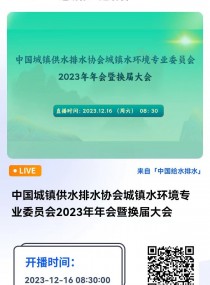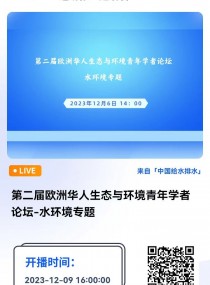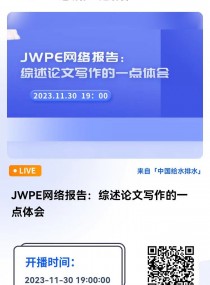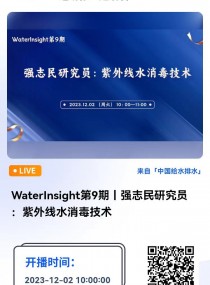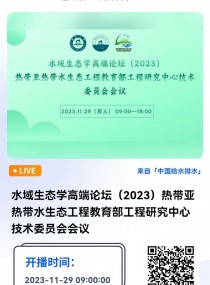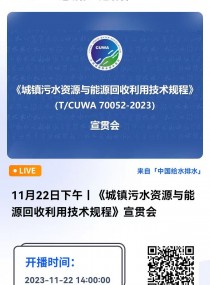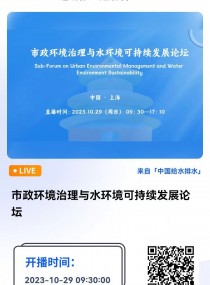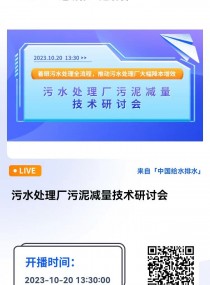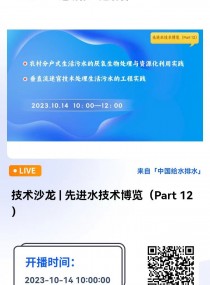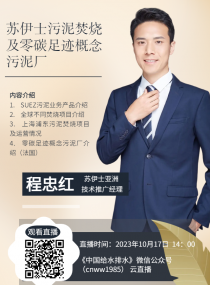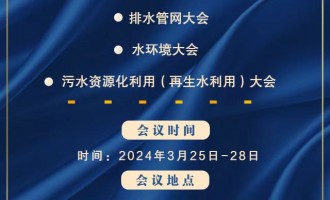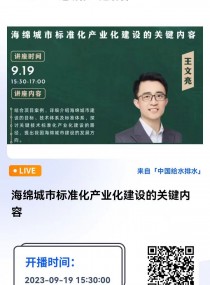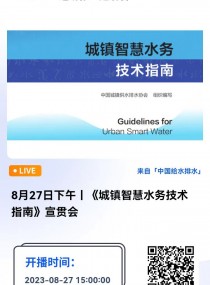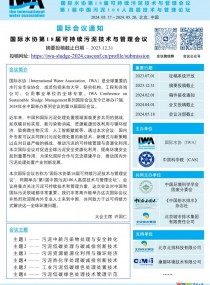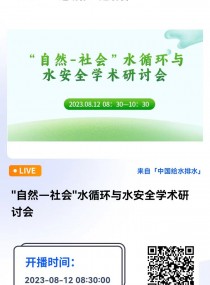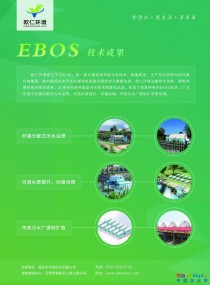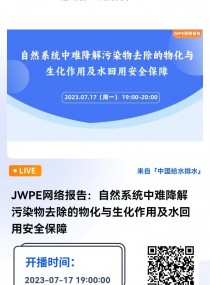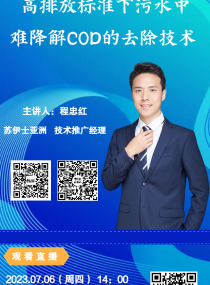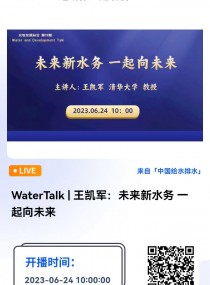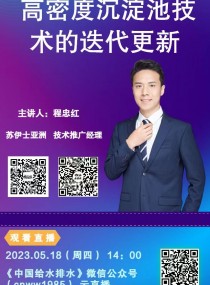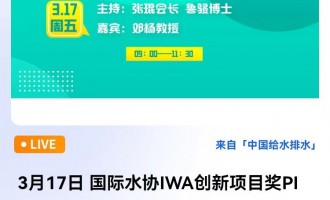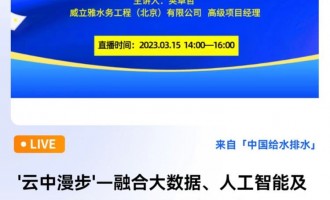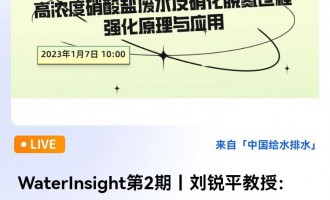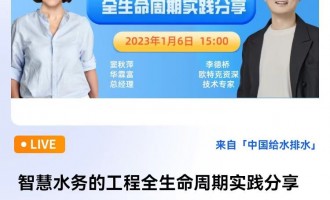歐洲水環境的觀察與思考
徐迅雷文/攝
沭陽斷水,太湖巢湖滇池藍藻水華綠如油漆;洞庭鼠患,淮河重慶濟南豫西洪水泛濫暴雨成災……2007之夏,中 國水環境問題空前暴漲。在全球變暖的大背景下,極端天氣氣候頻頻降臨;由于沒有良好的水環境底子,“水利”變成了“水 災”、“水害”。
水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要素。人類的所有文明,最初都發源于河流;沒有河流沒有湖泊,就沒有人類;人類是不可能離 得開水環境的;人類是環境的產物,又是環境的一分子;人類不可能高于環境,人類只可能融入環境、與環境和諧相處。
今年5月,筆者訪問歐洲,考察了萊茵河、施普雷河、美因河、阿勒河和盧塞恩湖等江河湖泊,關注到歐洲優良的水 環境,以及治理、管理水環境的經驗。給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萊茵河。何處江水綠如藍?只要看看今天萊茵河的片段。在我的 鏡頭里,流經瑞士巴塞爾市的萊茵河,色彩變化多端:在情人們幽會的“情人谷”一帶,河水藍得比翡翠還徹底,中國名詩“ 春來江水綠如藍”仿佛就是為這里的河水所寫的;在巴塞爾大教堂的望河平臺上俯瞰萊茵河,河水以綠色為基調,那木制渡船 漂移在河中,頗有點“野渡無人舟自橫”的韻味;車過跨河大橋,透過車窗所拍攝的,則是油畫色彩的萊茵河,“晴云似絮惹 低空”,河水有一種凝練的質感……這,都是歐洲水環境之美的縮影。
他山之石,可以為錯;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。歐洲水環境之變化,應該成為我們借鑒之經驗。
為河流“動刀”
萊茵河在地圖上畫了個“L”,拐角處是一個奇妙的城市—瑞士巴塞爾。巴塞爾是世界上惟一與三國交界的名城,左 前方是法國,右前方是德國。2007年德國旅游博覽會在首都柏林舉行,而瑞士的旅游博覽會則放在巴塞爾,作為媒體人士 ,我有幸參與報道了這兩個盛會。巴塞爾作為瑞士北部的邊境名城,它不僅是會展之城、文化之城、旅游之地,也是歷史上發 展起來的化工之城;萊茵河穿過巴塞爾,一座城市因此靈動起來。
美麗的萊茵河發源于阿爾卑斯山,全長1320公里,是一條著名的國際河流,主要流經瑞士、法國、德國、荷蘭, 由荷蘭灣注入北海;萊茵河流域面積為20萬平方公里,流域內生活著5000萬人,有2000萬人以萊茵河作為直接水源 。萊茵河中上游萊茵河河谷尤其美妙,它在2002年被評為了世界文化遺產,具有獨一無二的魅力;其環境優美是不用說了 ,更可寶貴的是積聚了兩千年的豐厚文化底蘊,沿途的古堡、歷史小城、葡萄園等等,“生動地描述了一段同多變的自然環境 相纏繞的漫長的人類歷史”;沿河發生了眾多歷史事件,演繹了許多傳奇,幾個世紀以來,它給無數的作家、畫家和音樂家提 供了無限的靈感。
通常人們把處于德國的、從科隆到美因茨近200公里的河段,看成是萊茵河景色最美的一段,其實再上溯到法國著 名文化名城斯特拉斯堡、上溯到瑞士邊境名城巴塞爾,萊茵河都是那么的美麗動人。然而,歷史上萊茵河并不都是安然無恙, 在上世紀70年代,由于萊茵河干流河道被高度渠化,兩岸密集城市排放的生活、工業污水使河道嚴重污染,魚蝦幾近絕跡, 一度被稱為“歐洲最浪漫的臭水溝”。尤其是二十多年前的“萊茵河污染事件”,是世界環境污染最著名的“十大事件”之一 ,曾給萊茵河帶來了巨大的生態災難。
1986年11月1日,在巴塞爾,桑多茲化工廠一間倉庫爆炸起火,1250噸劇毒農藥隨著百余噸滅火劑排入下 水道,進入萊茵河。劇毒物質構成70公里長的微紅色飄帶,以每小時4公里速度向下游流去,流經地區魚類死亡,沿河自來 水廠全部關閉,改用汽車向居民送水,接近海口的荷蘭,全國與萊茵河相通的河閘全部關閉。可是禍不單行,11月21日德 國巴登市一家化學公司的冷卻系統也出了故障,又使2噸農藥流入萊茵河,使河水含毒量超標準200倍。污染給沿岸國家造 成巨大的經濟和環境損失,以致好幾年萊茵河里無魚可捕撈,有人稱這次事故是“水工業的切爾諾貝利事件”;這一事件,載 入了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《我們共同的未來》這一著名的報告中。
痛定思痛,為了河流的健康,必須“動刀”了。此前成立的“保護萊茵河國際委員會”發揮了重要作用。該委員會是 一個非常有分量的“跨國組織”,主席當然要輪流轉,但秘書長總是由荷蘭人擔任,因為荷蘭是最下游的國家,最有“發言權 ”;委員會設有若干技術和專業協調組,如水質組、生態組、排放標準組、防洪組和可持續發展規劃組等;他們還把自來水礦 泉水公司和食品制造企業等“水敏感企業”都組織進來,使之成為“水質污染報警員”。多年來,他們切了一刀又一刀:19 87年,委員會通過了全面整治萊茵河的“萊茵河行動計劃”;1995年,起草了萊茵河地區“防洪行動計劃”;1998 年,締結了《萊茵河保護公約》。在《萊茵河保護公約》中,規定了締約方的種種行動原則:預防原則、謹慎原則、治本原則 、污染者負擔原則、污染影響不擴散原則、重大技術措施補償原則、可持續開發原則、環境污染不轉嫁給其他環境介質的原則 等等,都屬于“組合拳”。
“動刀”就是動真格:以前為了貪圖一時之利,建造了為航行、灌溉及防洪的各類不合理工程,被“動刀”拆除,兩 岸水泥護坡重新以草木替代;部分“裁彎取直”的人工河段,也經過“動刀”,恢復了自然河道。與此同時,各國全面“動刀 ”,控制生產與生活污染物排入萊茵河,對工業生產中危及水質的有害物質堅持進行處理,并減少河流淤泥的污染……動真格 的成效十分明顯:1994年,萊茵河支流中發現了洄游而來的大馬哈魚產下幼卵;2003年,排入萊茵河的水已達標,萊 茵河水終于變得清澈;今天,萊茵河的生物多樣性,已恢復到二戰前的水平。“拯救萊茵河”獲得了成功,從此,萊茵河不再 承受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”。他們的眼光放得更遠,整個萊茵河流域正在實施可持續發展的“萊茵河2020計劃”。
德國人曾經羞愧地說“萊茵河是一條工業之河”,但現在對萊茵河的重新評價是“萊茵河河水如今好得令人驚訝”。 今天的萊茵河,成了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一條河,是人與河流建立和諧關系最成功的一條河。
讓湖泊“休息”
如果說河流是人類文明的紐帶,那么湖泊就是人類文明的鏡子;這面鏡子能夠清晰地映照出人類究竟是文明還是野蠻 ,睿智還是愚昧。
在瑞士,我們訪問的首站是盧塞恩湖。盧塞恩湖的清澈湛藍如翡翠,那一種純凈讓我深切地感到,我們的桶裝純凈水 也不過如此。瑞士全國有1400多個湖泊,個個仿佛都是純凈水“罐裝”的。這是整個國家長期以來讓湖泊“休息”的結果 ,當然,這里的“休息”是積極意義的,并不排斥綠色旅游。
讓湖泊“休息”,就是不要去打擾它;而人類對湖泊的最大“打擾”就是化工廠之類直接排放污染物。讓湖泊“休息 ”,才能使其避免操勞過度,“未老先衰”。湖泊是會“老”的,湖水富營養化之后出現的水華藍藻就是湖泊的“老人斑”。 我國大量湖泊都已年紀輕輕就進入了衰老期,太湖就是典型。水利學者劉樹坤先生有個形象的比喻:長江是誰都來割一塊的“ 唐僧肉”,黃河是被吸干了“乳汁”的母親河,太湖則成了一盆污濁的“洗腳水”。只是現在這盆“洗腳水”已被涂上了厚厚 的“綠油漆”。
讓湖泊“休養”,才能讓湖泊“生息”,充滿勃勃生氣。但僅僅就湖泊說湖泊是不夠的,圍繞著湖泊的整個流域的水 環境都要修養生息。因為湖泊主要是河流匯聚成的,湖泊水環境的優化,首先有賴于河流環境的優化;河流整治好了,湖泊也 就治理好了一半。英國最長的河流塞汶河,就是一條長期以來修養生息的河流。人們對著名的泰晤士河很熟悉,但它是英國第 二大河;塞汶河長約338公里,流經英格蘭西南部,注入布里斯托爾灣;塞汶河流域是江河湖泊原生態的典范,因為它是一 條基本上不設防的河流,讓它處于自然狀態,任其漫溢;人類與河流進行的是“非對抗性游戲”,讓洪水瀟灑,人類并不去居 住,這就是與洪水相適應。
種種對江河湖泊的人工建筑,也是一種打擾。8月2日下午,杭州錢塘江潮水卷走30余名在“丁字壩”觀潮與游泳 的群眾,遇難十余人。正是有“丁字壩”這樣的人工設施,“誘使”人們上去玩耍,結果遭遇不測。與錢塘江一樣,塞汶河也 是一條涌潮的河流;塞汶河由于長期處于休養生息的原生態,反而更安全;而且人類離河流湖泊遠了之后,污染自然也少了。
原生態的河流、“休息”中的湖泊,少了堤壩等等人為建筑,也給生物留出了通道,這樣的水邊空間更加自然、舒適 ;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,并不是以“改造自然”為首選標準的。
替地下水“攔網”
當你早上一打開水龍頭,流出來的水像桔子汁一樣,這顯然不會讓你興高采烈,以為自來水公司改送“桔子水”了。 太湖藍藻暴發被迫停水時,那水龍頭里流出來的水就像桔子汁,而且臭味難聞。
歐洲發達國家的自來水都是可以直接飲用的,而直接飲用的水不是靠千般過濾萬般消毒取得的,水源本身就要基本達 到直接飲用的水準。地下水是歐洲2/3飲用水的來源,所以歐洲環境署特別重視地下水的保護,作了持久的努力。地下水一 旦受到污染,比地表水和江河湖泊的水更難自凈,需要花費數十年甚至數個世紀才能修復。所以,關鍵的是必須替地下水“攔 網”,防止化學品等污染物滲透流入地下水;同時還要保持地下水位在一定的水平。
歐洲水環境控磷已有半個世紀的歷史,其策略是洗衣粉禁磷和污水處理除磷。歐洲水處理技術是世界一流的。作為會 展大國的德國,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水行業展會—水處理技術與裝備國際展覽會,參展商通常都有2000個左右。法國經過 2003年造成數千人死亡的酷暑,2004至2005年干燥的冬季、2006年的低降雨量,使地下水位嚴重下降。法國 已經強制實行水定額配給制,限制農民的過量灌溉,并考慮今后實施更為苛刻的水配給制度。盡管歐洲水環境總體上已是相當 的好,但他們仍然有著強烈的水環境危機意識。歐洲環境署的有識之士,致力于推動出臺歐盟成員國全面防止所有來自各地的 化學品流入地下水的條款。美國同樣重視地下水,他們連馬糞的堆積都要作特殊的審批,以防止可能污染地下水。
相比之下,中國人似乎有個國民劣根性,就是只顧表面不顧內里,只顧上面不顧下頭,所以對“下水道”系統是不重 視的,一個城市 “下水道”的粗糙惡劣,只要來一場大雨就暴露無遺。青島老城區的排水系統如今還是最好的,可那是德國 人百年前在“租界”里鋪設的。我們對“下水道”系統的基礎設施都弄成了“腸梗阻”,就更別提與污水處理系統銜接、替地 下水“攔網除污”了,我國超過1.7萬個城鎮至今還沒有污水處理廠,污水于是就無遮無攔地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
“治污理水”不能晚點
水,是人類母親的乳汁;沒有了水,就沒有了生命,更沒有了人類文化和文明。你是要恐怖的水污染、水危機,還是 要美好的水資源、水景觀、水生態、水文化、水環境?我們最大的愚蠢,就是認識不到自己是通過戕害環境來最終戕害自己。
中華民族的水環境,已經到了“最危險的時候”,每個人都必須發出強有力的吼聲!污染性缺水嚴重,水危機已經大 量催生了“水難民”,也嚴重影響著百姓的健康。日前衛生部長陳竺說,13億中國人的健康不能光靠看病吃藥,“加強預防 和保護環境是根本”。我們應該樹立“治污、理水”的理念—污是需要治的,水則要管理、疏理。我們的水環境保護不能“晚 點”,為了水環境的健康,為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,必須痛下決心行動起來。
環境也是生產力。拋棄環境、追求GDP的發展,最終必將損失GDP。從本質上說,“水環境”不僅僅是水本身的 環境,它涉及到一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戰略,涉及到整個國家的制度環境。我國的環境問題,已越來越引起國際的關注。7月 底,美國總統特別代表、財政部長保爾森訪華,第一站就是考察我國最大的內陸咸水湖—青海湖,環境問題是保爾森此行關注 的一個焦點。
此前的7月17日,經合組織(OECD)在北京發布《中國環境績效評估》報告,給中國環保打了低分。報告說, 中國近半主要城市飲用水源不合格,約有3億人在飲用受污染的水,流經城區的大部分河流都不適宜飲用和垂釣,長江、珠江 、松花江等7個重點流域的水質仍呈惡化趨勢;中國河流1/3河段處于“嚴重污染”狀態,大的湖泊有75%的面積和沿海 水體有25%也處于“嚴重污染”的狀態;污染引起的健康損失將占GDP的13%……(7月19日《環球時報》)
《中國環境績效評估》是經過18個月的調研后作出的,它肯定了中國的環保努力,給出了51項具體建議,它敲響 的是“警鐘”而不是“喪鐘”。經合組織是“富國俱樂部”,他們已經成功走過了環境治理之路。發達國家水環境曾經的污染 ,不應該成為今天我們水污染的托詞,而應該成為我們避免重蹈覆轍的鏡鑒。
讓我們記住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在其名作《難以忽視的真相》中的一句話:“失去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忘記我們曾失去 了什么。” -